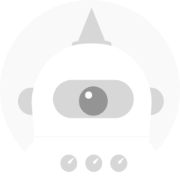图片来源:图虫网
《搏疫》是创业邦在疫情时期推出的栏目,以案例解析的形式,跟踪报道创业群体的生存状态、“搏疫”策略、经验分享等故事,以帮助创业者和衷共济,共克时艰。
作者 | 胡勇
编辑丨曲琳
北京正被大雪笼盖,户外人迹无踪,城市陷入白色死寂。
这等光景若发生在寻常年份,并无什么异样。然而,一场疫情倏忽而至,于是,一切都变得不再平常。
截至2020年2月7日下午14时,全国确诊的新型肺炎患者达到31223人,死亡人数达到637人。
疫病封锁了数以百计小区、城市,虚拟的游戏世界成为了百无聊赖的人们最主要的避难所。
一大批头部游戏成为了这次疫情迫不得已的受益者。据建投海外研究估计,腾讯旗下的《王者荣耀》在今年1月的流水约为90.84亿元人民币;中信证券研究团队预测2020年中国游戏市场的同比增幅将超过10%,其中移动游戏市场的增长则将超过15%。
然而,这只是游戏行业的冰山一角,对更多的游戏人而言,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游戏世界,这个春节及冬天都变得越来越漫长和萧瑟。
对数以万计的游戏人来说,他们不仅在和疫情战斗,同样还在和时间战斗。活下去的唯一诀窍就是熬过这个冬天等下一个春天及夏天。
对命运多舛的游戏业来说,即便被公认为不受疫情影响甚至更为利好,这仍旧是一个先喜后忧的故事。
在这个冬天,游戏和现实世界第一次如此紧密而悲伤地同步了。

死亡搁浅
疫病蔓延开来,刘秀预想随着状况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会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
他乐观地估计,在整个春节期间,他们手游的活跃用户最高可能会增长一倍,ARPU会有至少四成的增长。
刘秀他们做的是一款RPG手游,平时每日活跃用户不到两万人。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刘秀临时批了十多万的市场预算在春节前做一波突击推广。在公司的年会上,刘秀自掏腰包给策划和程序员团队各发了两万的红包。他希望产品能在来年肆虐起来。
世事的幸与不幸,总是相对而言的。
疫情以让人猝不及防的态势肆虐起来,随着感染人数不断增长的还有刘秀他们游戏的玩家和付费。贺岁档电影集体撤档之后,游戏的数据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峰值。
一切都和事先预料的那样,唯一超出刘秀估计的是,他也没有想到,这场疫情会蔓延得如此凶猛。
除夕前一晚,他到公司转了一圈,给回家前还在最后加班的几个人每人发了666元的红包,大家戴着口罩,没有过多言语。
整个办公室一片寂静,那一晚,刘秀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那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
临走前,他瞧着SOHO外国贸街头还在闪烁着的霓虹灯和空旷的街头,心中生出没来由的恐惧。

图片来源:图虫网
“我当时在想,如果这肺炎这么严重,要一直持续下去到底会是个什么结果。”刘秀说道。
过年的时候,刘秀一边盯着游戏的数据,一边盯着疫情的状况。
尽管数据增长超出了之前最乐观的预期,但是,即使在公司群里也没有多少人为此欢喜,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团队只有不到三十人,刘秀知道其中至少有四五个都是湖北的。
疫病吞噬着每个人的正常生活,刘秀原本计划的日本游夭折了,只能龟缩在家中。
在疫病蔓延的时节,时间本身似乎也变得粘滞了起来,每分每秒都变得如此漫长,在这样空洞而诡异的时间漩涡里,刘秀开始失眠了。
“老是做梦,莫名其妙的梦,梦见回到以前的学校,然后就跟《返校》一样阴森森的。醒来了浑浑噩噩,躺倒了又睡不着,就这样周而复始。”刘秀沮丧地说道。
更让他忧虑的是,游戏世界也随着现实一样渐渐崩塌了。
在农历初五达到峰值后,游戏活跃用户就开始逐渐下降,情况持续了四五天,刘秀焦急地询问运营团队出现了什么问题,没人能给出他满意的答案。
他联系上了认识的同行,却发现大家的状况都大同小异。
尽管有了空闲时间,但是,空闲了接近半个月后,玩家正开始逐渐逃离游戏世界。
刘秀他们的数据显示,在常规的春节假期结束后,活跃玩家的数量较之最高峰时已经下滑了将近一半。
“我问了一圈的结果,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大家可以干的事情太多了,手游是个碎片化的事情,十多分钟划水摸鱼的事情玩几个小时玩十几天,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和应用场景冲突的。”刘秀解释道,一边看着疫情状况,一边看着后台的数据,他的郁结集聚成悲伤。
“我们真得要扛不住了。”他以近乎哭腔的悲怆语调嚎叫道。
无能为力的刘秀翻出《死亡搁浅》(Death Stranding)玩了起来,在疫情改变着现实的这个冬天,唯一能让刘秀感到些许慰籍的是,他在游戏中获得数以千计陌生人的感谢。
“在游戏里面,我可以‘链接’陌生人,但,现实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只能隔离彼此。”刘秀颓然说道。

全境封锁
封城通告发布的前一天,马援打电话催促着老家的父母快些出城。
“还是晚了,他们本来就不想走,一来二去最后收拾妥当了也走不了了。要是那时候我嘴上紧点一直催就好了。”马援说罢,轻轻叹了口气。
对马援一家人来说,江城宛如围城,在里面的想出去,在外面的想进去,然而双方都不可得。
马援所在的团队开发的是独立游戏,中国的独立游戏开发者正经历着最好的年景,唯一的问题是,马援他们并不属于这样的开发者。
他们在PC上推出的塔防游戏一直不温不火,尽管已经在各个论坛社区投放了好几轮宣传,但是,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早在十二月,马援就开始和一些直播平台上的主播接洽,希望他们能直播自家游戏来导流。
谈了三四家之后,马援心力交瘁,要么对方要求的价码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算,要么是双方对规定播出时间和最后效果的谈判一直僵持着无法推进。
“谈着谈着,疫情就来了。找主播的人更多了,我们排不上号,就更难了。”马援说道。
春节是独立游戏大规模增长的档期,马援他们提前策划好了砸金鼠、推广得红包等活动。按照他们的设想,节前的这轮宣传能让游戏在2020年夏季前卖出一万到三万份左右。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的爆发和蔓延打乱了他们所有的规划和部署。

图片来源:图虫网
本来预计除夕前推出的新版本不得不临时跳票延迟到元宵节以后,官方理由是受疫病影响更好打磨作品质量云云,实际原因却让人哭笑不得。
马援他们最早的策划案是结合鼠年来做一个“天降金鼠,荡涤人间”的活动,所谓“金鼠”在游戏中就是被疫病感染的吉祥物,玩家要在新的剧情中解锁关卡战胜疫情。
随着局势越来越严峻,这个团队突然意识到,这个策划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大家在外面打听了一圈,所有的反馈都是一样的:做这个就是自找麻烦。
“我们当初脑子抽了还放了‘野味怪’,还有什么‘死城’要玩家去拯救,这要真放出来最后谁知道会是啥下场。”马援悻悻说道。
策划了两个月的新版本最终就这样付诸东流。
马援他们清楚,在春节什么活动策划都没有推出基本上就宣判了这个游戏已经一只脚踏进了坟地,他们手忙脚乱地开始计划来补救。
在发出跳票通告当天,戴着口罩的十多人挤在会议室,苦思冥想着应对的方法。
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与其坐以待毙毋宁断臂求生,他们决定在社区平台上发游戏key,用这样的方法来吸引新的玩家。
“我们里面有道具和皮肤,这些课金还算厚道。把游戏免费发出去,人家看顺眼了兴许还能扔几个钱不是?”马援说道。
这个游戏在整个春节期间一共实际发出了三千多个游戏key,马援拒绝透露这些玩家带来的课金收入,只是简单说结果“超乎想象”。
疫情仍然在持续,马援每日的生活和过去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两样。
他每天都要给父母打电话询问那面的情况,情况并不乐观,可是,他也无能为力。
在北京雪飘得最厚的那天夜里,马援一人打着伞在楼下漫无目的地溜达了好几圈,看到黄色路灯光下沸沸扬扬的飘雪,他说,他差点忍不住要哭出来。
“我走一路,走到最后,走一脚,踹一脚雪。我他妈当初一直催他们出来就好了,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呢。为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他忧伤而激动地说道。
马援最担心的是,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这场疫病究竟什么能结束?恢复到正常局面需要多久?
在此之前,他无能为力。
在FaceTime里无数次头脑风暴之后,没有人能给出什么方案来让这个独立游戏在局面正常后继续增长。
马援模糊而又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冬天,发生了很多事情,很多事情也永远地被改变了,再也回不去了。
在家办公的日子,他心血来潮重新下载了《全境封锁》(Tom Clancy's The Division),在残酷、寒冷、萧瑟的被封锁的纽约,马援孤独幸存。
“你还记得那个任务吧,我们一路杀过去之后,那个女NPC就在那里坐着,弹着钢琴,等我们。我喜欢这样的场景,事情结束了,他们也一定在家里等着我。”FaceTime那头的马援说完,别过头,像是要拭去落在眼角的灰尘。

八方旅人
成千上万个故事有着成千上万个开头,但它们的结局却只有两种,欢愉的与悲伤的。
在故事的中间,冯异面临着抉择,春节的时候要么留在沪上继续直播,要么回家并且因为累积时长不达标而要在年后恶补。
阴丽华的家在江城,那里有热干面和珞珈山的樱花。
她已经做了一年多的游戏主播,但是,却始终不见起色。
“我可能还是把这想得有些简单了,当主播不是要‘脸’和不要脸就行的。”她幽幽说道。
她所在的平台挂靠在一家国有企业下,尽管名头不小,但是,阴丽华清楚,这个平台恰恰是竞争压力最小的,她最初选择这里也是为了避免过于激烈的竞争。
阴丽华玩着各式各样的游戏,或者是看其他平台最热门的主播播的游戏,要么是时下最时髦的游戏。
可是,她始终没有出人头地,对一个女主播而言,没有什么比露脸更能吸引观众的了。然而,大多时候,阴丽华都是将摄像头关掉的。
“我不需要‘卖脸’,我觉得我游戏玩得还行呀,有时候也挺有节目效果的,为什么要露脸呀,就不。”阴丽华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多的几次露脸是在玩《健身环大冒险》时,那也是阴丽华后台数据最好的几次。然而,阴丽华不得不承认,玩这个游戏实在太累了,播了两三天之后,她已经感觉吃不消了。

图片来源:《健身环大冒险》
阴丽华只好停播,只是不到一周的空窗期,对她这样的尾部主播来说不啻致命的打击。再次播出时,看着后台的真实数据,阴丽华实在提不起兴致再对着空无一人的直播间说什么话。
以后,她不仅不露脸,甚至也不再说话。
“我就是喜欢,谁也管不了我。被管了二十多年了,现在终于自由了。”她说道。
在上海,她没有正式的职业,阴丽华很爽快地承认,她就是一个游荡在大城市里的无业游民。
这一年多的花销全是她大学时候兼职赚来的,现在她偶尔还会去酒吧驻场,大多数时候,她过着颇为闲适的日子。
每天睡到自然醒大概在早晨十点多醒来,消磨不多的时间吃完午饭,阴丽华开始线上的英语课程。到下午三四点,她或者看直播或者看书或者看电影。吃过晚饭,晚上七点多她就开始了自己的“非正式工作”。
事实上,阴丽华做的是一份自己根本看不上也不喜欢的“工作”。
即使在不露脸不出声观众寥寥无几的日子,她偶尔还是会吸引到几个穷极无聊的观众,发现她是年轻女孩后,总是会有让人作呕的骚扰私信让她不胜其烦。
最让她悚然的是,甚至有人能通过各种蛛丝马迹从她的直播间一直追查到微博、Instagram上,对方给她留言要去她楼下请她喝咖啡。
她拉黑了对方,将社交平台上可能暴露自己信息的内容尽数删去,在朋友家蜗居了半个月,待一切风平浪静之后才回家。
这些故事,阴丽华从来没有跟家里人说过,从大学毕业之后,她和父母就不再联络了。
“很狗血的故事,他们想让我去当老师,可是我不想,我想先走走看。然后大家就闹崩了,再也不说话了。”阴丽华淡然说道。
阴丽华有些失落地回忆道,小时候是父亲带她在神游机上玩《时之笛》(ゼルダの伝说 时のオカリナ),可是,长大后和她在就业上吵得最激烈的却是父亲。
最开始说要去SCAD的时候,父亲不置可否,直到阴丽华说要去学游戏设计,前者才明确反对。
“我能理解嘛,去那么个学校就够了,还去学什么游戏……可是,为什么不行呢?就因为我是女人?”阴丽华咆哮道。
自那以后,一家人就隔绝了。
看到疫情蔓延消息时,阴丽华踟蹰两三小时还是给母亲打了电话,刚听到后者的声音还没说上几句话,她的泪水就忍不住淌出来了。
阴丽华顽强地撑起逐渐沙哑的嗓音,努力不让电话那头的人听出自己的哭腔,不停地抹去推挤在脸庞上的泪水。然而,泪水似乎永远都无法擦拭完,她越是用力拭去,反而流淌得越多。
挂掉电话之后,阴丽华再也忍不住,一个人埋在枕头里猛烈地哭泣起来。几分钟后,电话又响了,她屏息静气了几秒,接通了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号码。
今年过年就回家吧,一家人一起……
父亲还没说完,阴丽华就挂掉了电话,她哭得更加凶猛,就像要把过去一年多憋闷在身体里的委屈和不安全都发泄出来一样。
她没有再犹豫,简单收拾好了,她定了最近的机票,决定回家。和她一起回家的还有Switch和《八方旅人》(オクトパストラベラー)。
在除夕前三天,阴丽华回到那座城,回了那个家。
“我不害怕,也不后悔,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家在哪里,人就在哪里。”在人们纷纷返工的时候,阴丽华在被封锁的城中发出这样的消息。
(应受访者要求,阴丽华、刘秀及马援均为化名)
本文为创业邦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创业邦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如需转载或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cyzon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