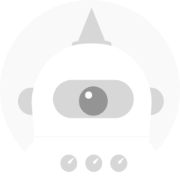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qspyq2015),作者刘子,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边走边爱国
多年前,我做背包客,始于东部的上海,西至帕米尔高原,南至南海,北至锡林郭勒大草原、黑龙江大兴安岭。
后来又时常出差,至今还未去过的省份,只有寥寥数个。祖国之壮阔,人文地理之多样,令我心神荡漾。
我爱这辽阔又悬殊,美丽又沉重的祖国。我承认,我的“爱国”,是贴近地面的,说不上主义,谈不上高度;不来自主流媒体,也不来自示范基地,而是始于足下,带着泥土的气息——只是我想,一个不真正了解祖国的人,所谈的“爱国”难免陷于形式和盲目。
现今出国热潮持续,富人向往欧洲、美国,中产偏爱日本、澳洲,再下至家乡小镇上的大妈,交两三千团费,也能潇洒去趟泰国,念念不忘。人们越来越开朗、开放,这是一国繁盛的体现,是好事。可回头一看,自己国家还没去过几个地方,自己家人都还不熟悉。
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不是感情,而是了解。一万公里外的非洲天天有人饿死,人们往往无关痛痒,但隔壁家死了一条狗,便摇头叹息——不是说人们没有同情心,只是非洲太过陌生,而隔壁家的狗时常出现,多少还熟悉一些。
因此日本人、澳洲人、欧洲人、美国人再熟悉,也不会把你当真正的朋友,而与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大地的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许多人却知之甚少,甚至充满疑虑与隔阂。
因此,当我打算前往西藏、新疆,许多亲戚朋友纷纷感到忧虑,“那边太乱,太苦,太危险,还是不要去”。这无疑是个“灯下黑”式的遗憾。
乡村之爱与哀愁
各异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塑造了东西南北不同的乡村之美。
东海之中,枸杞岛的渔村,渔业总体衰退,靠出海打渔谋生的人越来越少。“海上牧场”养殖业、旅游业却在提升,也有渔民牢牢守着自己的船,面朝大海只待扬帆。变化在自然而然中发生,这里依然保持着它自己的美,本地人、外来游客也享受着这份自然而然。
西北边陲,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天山深处的柯尔克孜族,阿尔泰山的蒙古族,忍受着长达半年的冰天雪地,多变而残酷的自然气候,远离城市与现代化生活,坚守着牛羊,每年转场数次,纵然艰苦,却感恩上苍与大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西藏喜马拉雅山脚下、尼木高原,贫瘠而淳朴的藏族村落,以地里的青稞、草地上的牛羊为生,每家的围墙外铺满牛粪(作为主要燃料晾干),苍蝇纷飞,却有着虔诚的信仰和干净的灵魂。脸上纵然沟壑纵横,却洋溢着安详真诚的笑容,路上遇见,真诚地邀请你席地同坐,分享糌粑、奶茶。
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西乌珠穆沁的牧民,天上白云,地上羊群,壮美辽阔,人烟稀少,凑桌麻将可能得骑马半天。我曾敲开一户陌生牧民的蒙古包,宝音一家待我如亲人,同吃同住,第二天附近的亲戚还都跑来看我。我给他们看北京天安门,尽管只有700多公里,一天的路程,但因为语言不通、文化习俗迥异,又或许困于牛羊,对他们来说,北京只能想象。
宝音的表弟巴特尔骑摩托带我到处晃悠,参加旗里的那达慕大会,但他骑不出草原——锡林郭勒草原20万平方公里,2个浙江省大小——草原上许多人终其一生,也走不出那茫茫草原。
故乡山川 + 乌苏里船歌李健 - 我是歌手第三季 总决赛
我们的乡村,正如迥异的自然环境,越远离城市,越融于自然,越充满多样的自然、民俗之美。也面临着各自不同的问题。
大体而言,中国东部乡村,多傍水而居,城镇化程度高,与城镇相融,工业化渗入其间,不乏家庭工厂,繁盛热闹,但多半环境恶化、民风退败;西部的乡村,多布于山谷绿洲,较远离城市,自然农牧,粗狂洒脱,但经济落后,生存环境依然艰苦,容易被时代的洪流抛下;中部的乡村,则多夹在两者之间,青壮年外出务工,徒留老幼,耕地退缩,既回不到过去,也找不到好的出路,左右为难。
再纵向看,越往南方的村庄,被现代化裹挟,在传统与现代商业文明间,人心躁动。到了广东南部,乡村与城镇逐渐融为一体,村民收入不错,一面投身发财大计,无所顾忌,一面本土意识、宗族观念强烈,面对寄身其间的庞大“北佬”,酿成不少社会矛盾和治安问题。
而越往北去,仿佛渐冷的气候,乡村越安于环境。除了城乡结合部,城市与乡村越来越泾渭分明。到了东北黑龙江,地广人稀,村民越重家庭,安土重迁。该走的都走了,留下来的自幽自默,心安理得,农牧、林业仍是地方重要经济支柱。村庄倒是人丁兴旺,社会发展却停滞不前。
城市与乡村,问题在哪里?
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同一档次的城市,颇为相似。差不多的CBD、新城区,差不多的高楼大厦、商场超市、娱乐场所,差不多的中山路、南京路、北京路,差不多的拥挤、行色匆匆的行人、忙碌的上班族,差不多的星巴克、肯德基、西餐馆、川菜馆、湘菜馆、沙县小吃……
天南海北的大小城市,围绕着“全球化”“工业化”“去农村化”三大主题,价值观、思想高度统一,标准化运作,逐渐把天赋不一、各自美丽的面孔整容成一个模子,终于像满大街的韩国标准化美女,初看很思密达,多看容易脸盲。
及至西藏、新疆、内蒙的偏僻小县城,有了国家的资金,发达地区的对口扶持,无论自然环境、本地市场、风土民情,也要先建起漂亮的办公楼、豪华的招商大酒店、大型的城市公园,繁华的步行街、城郊的工业园区,连满街的房地产广告也是不能少。
差不多的城市,导致差不多的问题。例如对“新”的痴迷,全国县及县以上,各类新区的数量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34亿——二胎已经不够用,全国人民还得再努力。而大大小小的事情,“产业方向、区域发展方向、投资方向、就业方向、补贴扶持与转移支付方向,都由政府说了算”。
因此城市问题主要在于,管城市的人太多,用力过猛,需要松绑。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很快,人民不介意它慢一点;我们的市长已经很累,企业不介意他轻松一点;城市的管理已经很交叉,市场不介意他们少管一点。
李总理也曾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老子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只有把束缚老百姓手脚的绳索都解开了,才能真正发挥13亿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大家都放松一点,也许对城市的发展更好一点。
与城市相反,乡村的问题在于“没人管”。
当然,这里的没人管是相对的。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必然关于三农,可一个“中央一号文件”概括不了4万多个乡、66万个行政村、261万个自然村的问题,一个“城镇化”、一个“新农村建设”,概述不了农村前途问题,一个农业部、271亿的财政支出(占34万亿总支出的0.08%)解决不了5.89亿农民的发展问题。甚至农业部三公预算1.1亿,也仅占中央部门三公预算的1.87%。突出国外、管工业管城市管建设的部门还时常出国考察,落后别人的、管农业农村的部门是否可以多要点钱,多出去学习一下?
国家对三农倾注了较大力量,正确的扶贫导向、强大政府执行力下,绝对贫困已消除得所剩不多,农民因为自然灾害、疾病等原因“活不下去只好去死”的情况已经基本杜绝,现今的农民已不再担心“活着”的问题。
到地方政府,开始打折扣。比如,罕有谁以“农业大市”为荣(农业难道可耻?),罕有主管农业的官员任职常委;你跟市长、县长谈工业、谈招商引资、谈房地产,大门敞开,你约他们谈农业农村发展,对不起,恐怕领导实在没有时间。
再到行政管理末端——乡镇政府,政府官员既不需要懂农业,又不需要靠农民吃饭(财政主要靠工业和上级拨款),既无关乌纱帽,又无关政绩、升迁,农业和农村工作就显得随意和乏力。比如,从分工上,农田、水利、畜牧、种植、新农村建设……往往由不同干部兼任,仿佛只是为了平衡官场。而真想做点事,既缺乏专业,又无财权、执法权,只能听天由命。
城市可以“标准化”、可以“拆——建”、可以举债、招商引资、抢钱抢人,乡村则不行!东部与西部的乡村,城郊与偏远的乡村,平原上与山区里的乡村,奔小康和求生存的乡村,有资源的和啥都没有的乡村……面临的问题都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农村问题,远比城市问题复杂。
也许,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也可以改一改,能把城市发展起来不算真本事,真要有本事,把农村也发展起来!
为什么没有“乡村改革”?
历史证明,最适宜乡村的治理模式,也许还是“自治”。
千百年来,皇权不下县,乡村靠乡绅治理,“以中国之大,全由官府去治理社会的角角落落,成本之高难以承受。从宋到清,中国人口不断增加,官僚数量则增幅不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宗族与士绅在基层承担了‘扶济族众、化解纠纷、教化子弟’等责任”。
乡绅、村“领导”,由民众公认、推举,权力的基础源于公众的承认和支持。一般由有资历、威望的人担任,而且“单靠财富本身也不能给人带来权力和威信”。此外,乡绅并非职业,“得不到直接的经济报酬,但由于为村里人办了事,他们也乐于享受声誉,接受一些礼物……他们在村里所处的领导地位也有助于他们保持特权的工作,如当教师,当丝厂厂长等”。
譬如我的小外公(外公的弟弟),就曾是村里的干部。他写得一手好字,掌管村委会账目,温文尔雅,颇有威望。逢年过节,由他主持宗族祭祀活动,乡邻们也常来求对联,村民之间有矛盾找他做中间人,有什么诉求也会向他反映。后来年纪偏大,乡政府要他让位给年轻人,被罢了“官”,不几年患病去世。村庄失了凝聚力,逐渐衰败,现在要凑一桌麻将都困难,也许过不了多少年,那个“李家村”就将消失在地图上。
他要是还活着,年纪跟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乡镇企业家类似——他们是最后一批“乡绅”集体,有能力,有闯劲,肯担当,带领村民致富,受到村民们的拥护,既是乡村的“领导”,也是意见领袖、精神领袖。只是随着时代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乡镇企业风光不再,加上新经济和新思想的冲击,他们已整体退出历史舞台。
乡绅阶层的权力真正源自人民,所获得的,除了声誉,也需要从带领乡村发展中才能获得实际利益。他们源于百姓,又服务、带领百姓,才能成为衔接政府和村民的枢纽。
诚然,现今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制度也是自治性质,“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民主自治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村民直选村主任。实际操作过程中,权力往往掌握在村支书手中,而村支书由上级乡镇政府任命,甚至直接兼任村主任。
选举过程也不甚如意,前些年,“由于乡村深厚的宗族意识(很多村民根本不顾实情,先投本家人一票再说)和小农阶级的局限性(一桌酒席换几张选票,直选成了村里有钱人的金钱游戏,选举还未开始,村里东头西头就先吃上喝上了),直选搞得一塌糊涂,糟不可言,丑闻百出。最后选上的人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本着毫不利村专门害人的精神,把村里的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接下来便是群众上访,结果乡镇党委政府表态,这是你们自己选的人,我们拿不下来。”
因此,以往选出来的许多村干部,往往是有势力甚至欺压百姓、涉黑的,选上了也加紧贪腐。近些年政府监管加强,已经好了很多,但群众对干部的不信任难以迅速扭转。同时,村委会的主要工作也逐渐简化为完成上级指派工作,及维持村委会基本运转,导致“干部干,农民看”,也就在所难免。
一般来说,只要村干部不犯错不出事,就能持续干到退休。真要让他们带领村民改变现状、求发展,困于资源、能力、立场等,实在是强人所难。
我老家所在的村是典型的中不溜秋,地处中部省份,既不大也不小,离县城既不远也不近,既不富裕也不至于很穷。
我们村现有村干部5人,现任村支书由上级委任,已连任3届。五年一届的村主任选举,也已成为一个形式。不知道谁提议,原来的村会计在村里干了几十年,快退休了,就选他当村主任,解决下人家的养老问题——村支书、村长拿的是国家工资,年收入2-3万,由国家交社保。
地方经济落后,村里没什么“油水”,大家对谁当村主任,兴趣不大。加上村民选举意识本来就欠缺,又随着国家取消各种农业税,除了建房,平时基本不需要跟政府、村干部打交道,因此对选举更加漠不关心。选票发到各个自然村,村会计村民们都认得,心中有数,懒得去领,“你选谁我就选谁”,有人不会写字,“你帮我代签就行了”。
还不如学校选班干部,起码得上台演讲、集中投票、公开唱票,热热闹闹。“你当爹,我当妈,他当儿子,就这么定了”,原本神圣的乡村选举,也就成了孩子们的过家家。
虽是自治,在村民眼中,村支书、村长已经是“官”,吃的是“公粮”,完成的是上级交代的任务,代表的是政府,与乡村自身的发展越来越“无关”。反之,在地方政府看来,村民自治,就是把权利赋予广大农民,你们不好好用,还玩“过家家”,这个我也没办法;再说,我一不要你纳税,二不靠你吃饭,“闹事”倒越来越在行,大家最好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多开心。
结果,当前乡村,自治不像自治,行政管理不像行政管理,呈现各自求生、放任自流的状态。
如笔者在《乡下集市的春天》所析,千百年来,广大农业人口第一次真正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迸发出强大的生产力解放,但是除了外出务工贡献廉价劳动,并无可释放的途径。而当前的乡村治理体制,从投入、重视程度、管理水平、人才建设、专业能力……等各方面,一直停滞,已难以适应。因此,迅速解放的生产力,与落后的乡村治理之间的矛盾,也就成为当前乡村发展的主要矛盾。
当我们谈改革,总热衷于“经济体制改革”、“供给侧改革”、“国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等时髦话题,却罕有人关注到乡村治理更亟需改革。
上一次乡村改革是1978年,小岗村人签订“生死契约”,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接解放了十亿农民的积极性,整个社会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经过40年的发展,5.8亿农民已经整体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需要又一次改革的引导。
“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慢慢消失,但是中国人口的质量红利还有巨大的空间”,这样的改革一旦成功,将激发出怎样的生命力,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又将进入到怎样的一个层次,充满无限的“想象空间”。
那么,这次改革谁来推动?
为什么不组织起来?
乡村自治,不能坐等改革,也需要自发的组织、探索。
发达国家都实施“农业保护主义”,注重保护农民利益,地方上的各种农业协会也往往联合起来,争取、维护自身利益。
譬如,日本的农民就是一个相当抱团的团体,拥有高度组织性,由全国和地方日本农业协同工会统一发声。农业协会最重要的诉求是提高农民收入,维护农民利益,为了自己的选票,日本政府往往只能照单全收。
农业协会由于站在农民立场,获得农民巨大支持,因此“对下”也有组织力、推动力。譬如,日本著名的宫崎“太陽のたなご”(太阳蛋)品牌芒果的诞生,就源于当地农民组织的成功运作。
宫崎原本不产芒果。1984年,当地果树技术会会员在前往冲绳取经蜜橘的过程中,吃到冲绳的芒果,念念不忘,于是决定培育。试种过程中,问题不断,但在几家农家的坚持与不断改良下,花了十年时间,才诞生这一高档品牌。
诞生艰难,维护更难。当地农协会对“太阳蛋”严格控制,数量、大小、色泽、香甜度,只有达到标准的才能冠以品牌名出售,以保证每一个芒果都毫无瑕疵。
此外,统一包装、营销、推广也是重点。今年春季的拍卖会上,两只一公斤重的“太阳蛋”芒果拍到50万日元(人民币3.16万)的天价。而拍下芒果的人表示,他之所以以这么高的价格买下这两颗芒果,意在表达对果农的致敬。
事实上,在我国的部分地方,亦不乏政府组织、整合一些区域农产品品牌,并在CCTV“精准扶贫”上进行推广,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广,多是临时的“任务”性质,效果难以持续。
中国的乡村太广袤,像老班章普洱茶、西湖龙井茶、赣南脐橙、阿克苏糖心苹果这样真正有天赋、有市场号召力的农产品品类还太少,而且也往往是区域内茶农、果农各自为战,离协作、离真正的品牌还太远。更遑论大多数乡村并没有这样的自然禀赋。
经过多年耕耘,农业硬件已得到巨大改善,北方早已机械化作业,南方也在加紧园田化,乡村规模化生产、职业化农业已经成为趋势。硬件改良后,“软件”的提升就显得尤为重要,观念、技术、组织、差异化、品牌、分工、协同、销售、推广……这一系列软件,亟待提升。
而这些改变,靠政府来组织,无疑还是看天吃饭,毕竟政府不能代农民种地、做决策、干销售,最根本的,还得靠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开放学习,找出路,尊重市场,尊重技术,艰苦奋斗,二次“创业”!
而政府要做的,是改革体制、加大扶持、因地施政,依法严厉打击食品安全问题。社会要做的,是媒体多关注积极的方面,去报道、扶持优质的农产品,而不是成天贬低国内农产品、渲染食品危机、制造人为恐慌;是大学、研究机构走上田间地头,与农民一起,去发掘、培育本地的土地可能性,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是金融机构将目光从烟花乱放的空中转移到扎实稳健的土地,增加对农业投入产出速率较慢的容忍度,甚至出现一家格莱珉“穷人”银行式的乡村银行……
只有当管理者、社会各界和农民站在一起,一起唱响这支美丽深沉的乡村之歌,这个时代才不会撕裂,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才会真正值得我们骄傲。
本文为专栏作者授权创业邦发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创业邦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cyzon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