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到了2002年,“泡沫”仍然是互联网行业的主基调:根据股价变化,截止2002年10月,“dot-Com(科技互联网)公司”们已经蒸发了大概5万亿美元的市值,大量公司被指控不诚实误用股东资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连续对投资互联网的机构开出巨额罚单……然后多年的大趋势推动了“鄙视链”的形成,人们开始普遍有理有据地默认“互联网公司”都不做什么正经生意。
对,是有理有据地默认。比如有研究机构复盘千禧年的“互联网泡沫”事件,发现经历过泡沫冲击的dot-Com公司,实际上有一半能活过2004年——这看上去多少能证明“互联网并没有被严重高估”,可当时的分析师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得出了两个很“经济学”的推论——公共财富涨跌和个体公司的生存没有必然关系;网络经济的参与者体量都太小,感受不到资本市场的动荡。
很多年后,韩寒就在《乘风破浪》里致敬了这段历史:在经常给人定性的老警察眼里,学计算机的小伙子“化腾”,是个不需要过多解释的无业游民。
当然了,这一年也不适合定调为“悲观”。
那是中国“入世”的第二年,许多曾经被媒体们大书特书的“入世承诺”开始兑现,其中就包括数码产品的大降价,越来越多的家用电脑把价格设置在四五千元的区间里。虽然从数字上看和《我爱我家》里傅明老人购买的DEC基本相同,但操作系统已经从基于MS-DOS的windows3.2进化为开创“商务互联网”新纪元的windows98/2000,处理器从286、386变成了奔腾赛扬、奔腾III,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来到了6280元,比90年代初实际增加了一倍多。
这样的转变,让互联网泡沫的意义变得辩证起来。中国网民不需要等待产业的成长,就拥有了大量的现成产品。而大量真实的使用体验,最终汇聚成了一种积极的消费热情:互联网,真的能给生活带来大不同,真的能让自己跑在时代前沿。
以至于到年终盘点的时候,数据“发达”到了这种程度:上网用户人数达5800万人,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网络游戏用户数807.4万,其中付费用户达401.3万,占到了总数的约50%;75.46%的被调查者对互联网收费表示可以理解,有7.98%的被调查者表示将完全接受即将到来的互联网收费时代……
“人民网”记者曾给出评语“(互联网行业)非常务实地立足中国本土,大踏步走向网络新时代”。旧时代可能指的是以“四通利方”为代表的BBS时代,新时代则或许是描述被智能ABC赋能的“大虾”们,逐渐取代用五笔打字的媒体人和城市中产成为网民主体。两者的区别是,后者享受“新表达方式”带来的新鲜感,而前者则第一次拥有了“对外表达”的能力,人们都指望着通过聊天室、个人烘焙鸡参与到更大的世界里,展现出来的表达欲丝毫不亚于现在的朋友圈和微博。
在这样热烈的氛围下,2003年的春天来了。
2003年的中文互联网已经表现出了极强的当代感。想象一下,以下哪个场景发生在2003年?
A.在一系列重要的公共事件、国际时事正在发生的情况下,娱乐圈事件依然占据了信息流;
B.互联网开始把目光投向五环外,无数县城、小镇被推动着进入了公众视野;
C.网民们感受到了内容表达方式上的“局限”,无数旨在解决“表达痛点”的新产品开始上线。
答案是:全都是。
4月,噩耗从香港文华东方酒店传来,媒体们迅速打开了选题库匹配上了热点:回望经典作品是一条线,事件原因调查是一条线,圈内反应拼拼凑凑也能成为一条线。但互联网人认为可以探索出一条新线,于是门户网站上多了许多新栏目。

搜狐上线了万人签名活动,网友们只需要留下“姓名、电子邮件或QQ号、发言内容”,就可以参与精选CD、电影套装VCD等周边的抽奖。抽奖具体还分随机和编辑精选,随机是幸运奖,面向所有合规的参与用户,精选是“技术奖”,增设了一些“文学门槛”的同时,还额外提供一些“非实体”奖励(比如他们的留言会单独在搜狐娱乐频道开设一个页面)。

现在人们给这条新线取了一个名字,叫做“UGC”。负责策划、引导、整理UGC内容产出的全套工作技能,又独立成为了一门职业,有的企业把它归类为用户运营,想着“拉新促活”,有的企业把它设置在内容运营里,用来展现自己的“优质用户群像”。
甭管怎么分化吧,能够拥有跨度达十多年的进化过程,足以证明了当时策略的立竿见影。新浪就对友商进行了统计,发现“哥哥,散落在人间的天使”网络纪念馆,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访问人数就已经超过了15万,最高点击量高达4000次/分钟。
作为参照对比,一个多月前,中青网发了一篇“结案报告”,表示他们策划的“学习雷锋40周年”网上纪念堂,在上线9天的时间里,收获了23万的访问人次。中国足协应该也很羡慕,因为他们发现联赛上座率严重受到2002年“甲B五鼠”假球丑闻的影响,一轮联赛7场比赛的总入场人数最低可以只剩8万9。

有新发现,就有新问题。《扬子晚报》的记者就在他们当地(南京)的网吧发现,很多人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网络聊天”,正在想尽办法搞些新花样,比如“对骂形式进行网络聊天”,据网管反映这种行为偶尔持续通宵——也不知道他们算不算“最早的职业喷子”,但可以肯定这是“网民变多”的结果,当“上网”不再是有经济门槛的“少数人行为”,“网络世界”只能越来越还原现实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北京和广州的民警们应该也有同感:自从网络聊天室这个“陌生人社交产品”风靡互联网,他们的工作变得复杂了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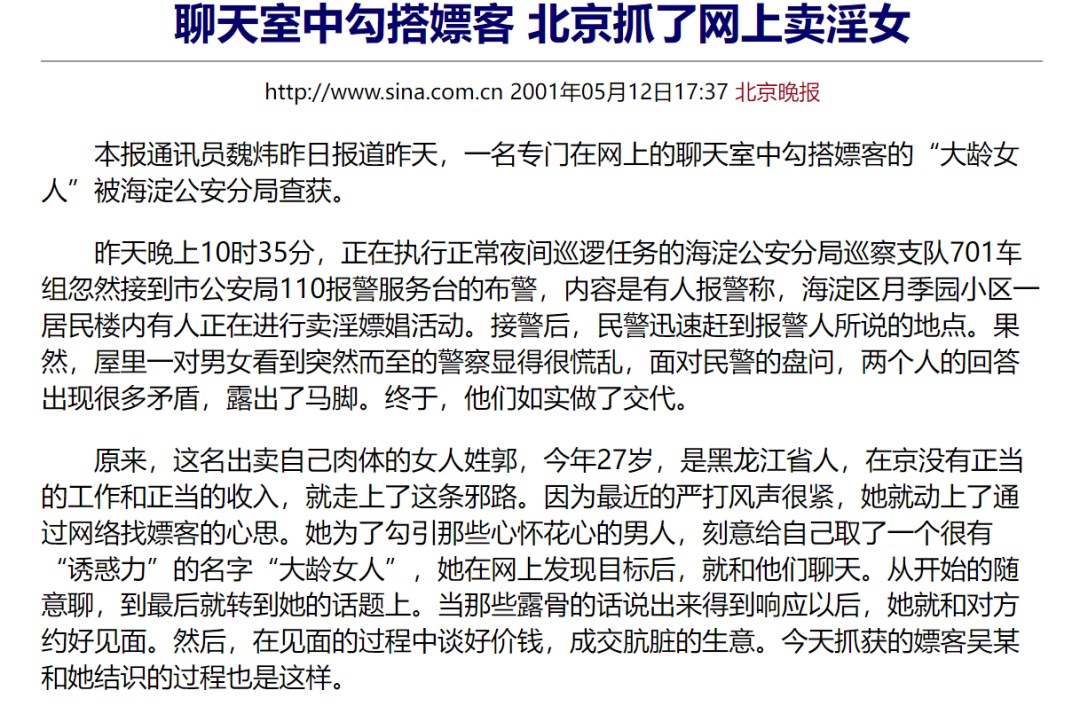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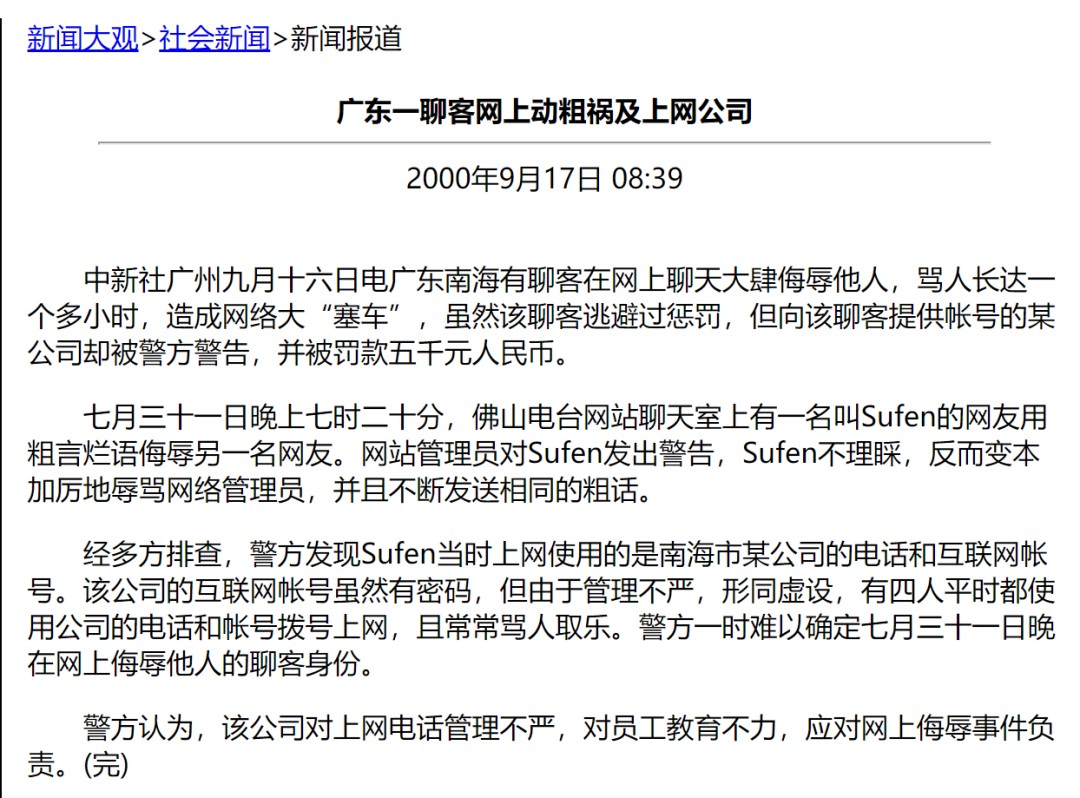
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人士也开始打马虎眼。3月的某一天,各大媒体忽然开始抢发新闻“比尔盖茨死了”,然后大概花了两三个小时又开始抢发新闻“这是谣言”。目睹了全程的网友们,给出了非常克制的评价,“善于学习的IT精英已经把娱乐圈‘狗仔队’作风和作秀行为揣摩利用地无以复加,举手投足都是戏”。

陡然的形势变化,容易让理想主义者变得保守。天涯就选择在2003年4月暂时关闭“聊天室”功能。官方把这次“关闭”描述为“改版”,目的是调整“改名”“点歌”“特效”等功能,然后争取点时间重新思考一下“会员等级(类似于QQ等级)”“聊天室管理员”这些机制。
通告的评论区里异议的声音不少,有人呼吁应该开放“游客”(也就是非注册用户),有人在公告十多天后质疑“改版的时间怎么这么长”,网管是不是“非典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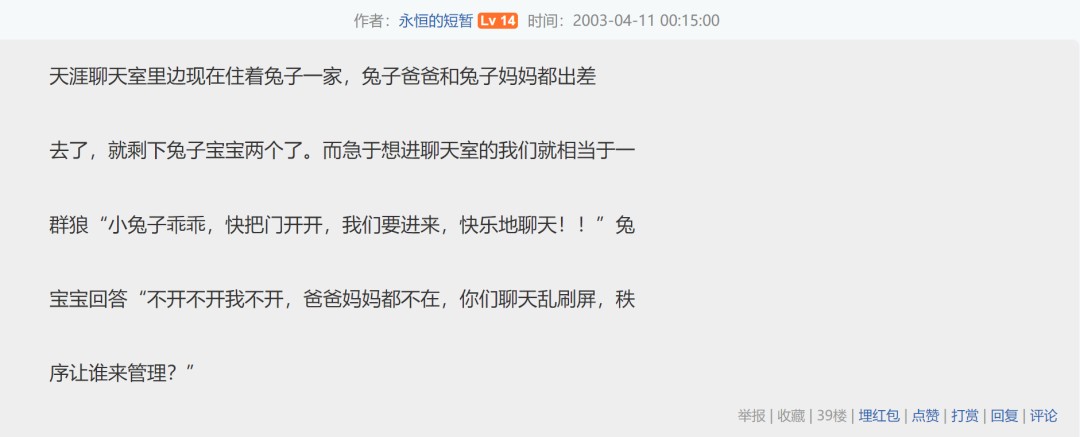
实用主义者嗅探到了机会。敞开了聊天不可控,那咱们升华一下呗?从北京大学的心理中心教授丛中博士,到冉冉升起了足坛新星郑智,学者、演员、歌手、知名主持人、体育明星陆陆续续出现在聊天室里。更大的野心藏在“名人互动”的页面设计里,像什么“新浪网-中国足球队唯一互联网合作伙伴”“话剧《圣人孔子》专题”。
整合营销、渠道运营的影子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传播理念呼之欲出,并将在几个月后因为一个女人的“露骨日记”大放光彩。届时,人们将重新思考“媒介”和“媒体”到底哪个重要。
不过这些都是上帝视角。“蛋糕会被重新瓜分”只是理论上的事,没人能准确预判理论兑现的周期是多久,更何况蛋糕看起来还足够大。所以“传统行业”对未来的期许,还能够专注地停留在对“社会价值”的讨论上。比如2003年《南都娱乐版》的新年致辞,就是这样写的:
“在2003年,我希望,既然八卦无法停止,那就来得更猛烈些吧!这个八卦不再仅仅局限于某几个人身上,而是发掘一切有八卦元素的明星和事件,让他们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我们先娱乐,在娱乐之余还是娱乐,或者表达一丁点关怀。让八卦来解放我们的郁闷,坚持在八卦中寻找快感,即使没有,也要假装有!
……在2003年,我希望,在娱记这个行列里出现更多更优秀的“狗仔”。“狗仔”们以“天下”的名义四处奔走,令那些隐藏在黑暗角落的某些丑恶或者人性无处藏身。”
有点像2020年初的微博热搜#我怀念娱乐八卦占据热搜的日子#,但不完全是,“强调谨慎地探索”和“呼吁合理地分配注意力”显然是两条终点不同的路。

网游被认为是“新时代新问题”的集大成,因为它能够承载的东西足够多,能帮“上网”大手笔地接管日常生活——社交,就像魔力宝贝、石器时代、传奇里的家族或者帮会;审美,西山居已经想办法把“江山社稷图”带进了剑侠情缘里,在越南完成了出海壮举;恋爱,就更不用说了,在这个能视觉上提供花前月下、情绪上能提供快意恩仇的虚拟世界里,不谈恋爱才是怪事——但距离又是实实在在的。
在不解决“最后一百米”的情况下谈日常生活,麻烦事就多了。有玩家会在网上发帖,寻找在游戏里M(音密,私聊的意思)过女网友,希望能够延续(萍水相逢),评论区分成了两派:行动派,用自己线下奔现做背书,鼓励楼主拿出点实际行动;理性派,似乎更擅长使用搜索引擎,质疑楼主收到的照片是搜来的,“那是个人妖,想骗你装备”。
宁财神就对此深有感悟。他把类似的故事写在了情景喜剧《网虫日记》里,黄晓明、吕小品梦想着在网上找到美女房客,没想一见面大家都是抠脚大汉。
《三联生活周刊》援引了一项来源不可考的网上民意测验,列出了“网络十大罪状":网络外遇、垃圾邮件、网络谣言、网络上瘾症、网络色情、网络并发症、网络赌博、网络购物狂、网络疏离症、网络假民主。在ADSL时代,网游至少能命中了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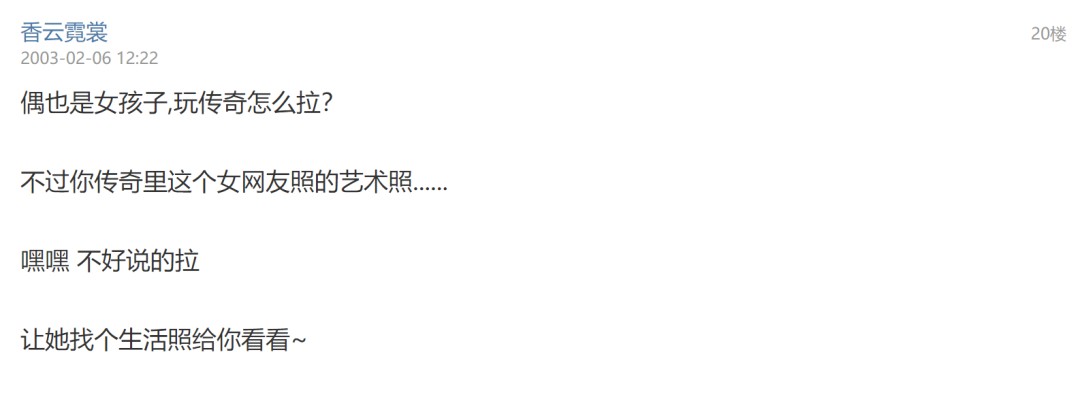
好在这些问题都是新鲜的,人们对新鲜感有天然渴望,歪打正着地为“解决方案”争取到了足够持久的注意力和参与意愿。紧接着,一场分工明确的“上网病”会诊开始了!
1月,政协委员朱尔澄拿出了一份民盟组织的调研报告,为这场会诊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认为“成瘾者与父母的职业有关,与父母了解、指导孩子使用计算机上网的认识及能力有关”。支撑的数据是北京中学生上网成瘾者的比例达14.8%(初中生为11.8%,高中生为15.97%),有54%的中学生对家长隐瞒了自己玩游戏的真实情况,但近一半(49%)家长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玩电子游戏。其中父母亲为高中文化程度的成瘾者居多,父母学历在本科以上者,成瘾率明显偏低,工人家庭的学生成瘾者比例偏高。
于是首先要解决“大家都上网”的问题,只有熟悉敌人才能打败敌人,“家乡论坛”进入繁荣期,媒体和互联网企业合作,请“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来聊一聊。解决“上网难”的Saas企业被热捧,一开年就有个叫“用友安易”的公司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成立,帮全国人民展望了一下“广阔的电子政务发展蓝图”。

没电脑也没关系,有手机就行,GPRS的商用正在大踏步实现,4月下旬业务就要展开到珠峰大本营去了。服务商们承诺,有朝一日发彩信、看图文直播奇才的乔丹、下载《八度空间》高质量mp3、下载刘老根.mp4都不是问题。
互联网公司觉得用不了那么久,传播学理论上“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可以提前,“短信”就是油门:你可以用短信订阅网站上的内容,也可以用短信转发网上的见闻,发给那些不会上网、没时间上网的朋友;如果你成为我们的注册用户,我们还可以帮你免费发短信。
网易泡泡就打了这么个算盘,再加上支持“头像上传”,一度严重冲击到正在执行“声讯台收费注册”机制的QQ。“声讯台收费注册”是一个值得单篇开题详聊的行业故事,当时就有人写了一篇非常辛辣的文章进行声讨,标题叫《腾讯QQ,你做的太绝了》,作者计算的单个QQ号注册成本是1块6。2003年的春天是绝唱,终结点是当年6月,腾讯以庆生三周年为名,重新开放了QQ号免费注册。

然后是寻找一个榜样。17173发起了“中国网游调查”。在指导部门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的指导下,“调查”一共设置了七大奖项,分别是最满意的客户服务、最满意的游戏画面、最满意的游戏音乐、交到朋友最多的、最受玩家喜欢的、现存玩家最多的、玩家最文明的。最后一个不太好理解,编辑进行了备注:可以理解成游戏里骂人骗人少,玩家最有礼貌。
关心阿里巴巴、卓越网、易趣网、当当书店、西单IGO5、莎啦啦鲜花网为什么会成功的人变多了。汪延、王峻涛、王树彤、邵亦波这些名字经常一起出现在新闻标题里,有时候谈的是“电子商务前景”,有时候谈“网络购物要讲诚信”。

当然理性分析,这很有可能是PR的成果。比如易趣,就在2002年刚刚拿到ebay的投资,三千万美元出让了三十三的股份。公关传播算不上什么新行业,功能早就得到过一票专家背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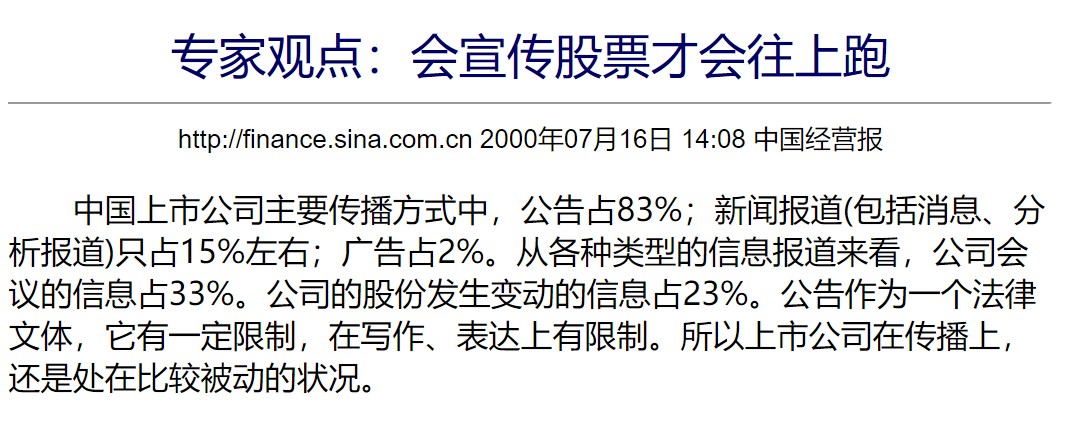
但很少有人热衷于指出“软文”,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在人们还在争论五笔和全拼哪个打字速度最快的时代,发表一篇长文章是一件让人肃然起敬的事;另一个是,跑邮局去汇款收货真的太麻烦了,技术革命你快来吧。

北京女孩袁日涉成了风云人物。她在前一年刚刚完成“献言献策,“设立儿童环保奖”的提议被北京市人大代表采纳,后一年她成为了“站长”。据媒体报道称,在那段特殊的时期里“浏览过这一网站的,无不被其乐观的童心所感动所鼓舞”“一个红领巾表现出的精神境界让人可敬可佩”——“鼓舞”似乎有保质期,6月有人因为“反感把正能量当生意”,选择把网站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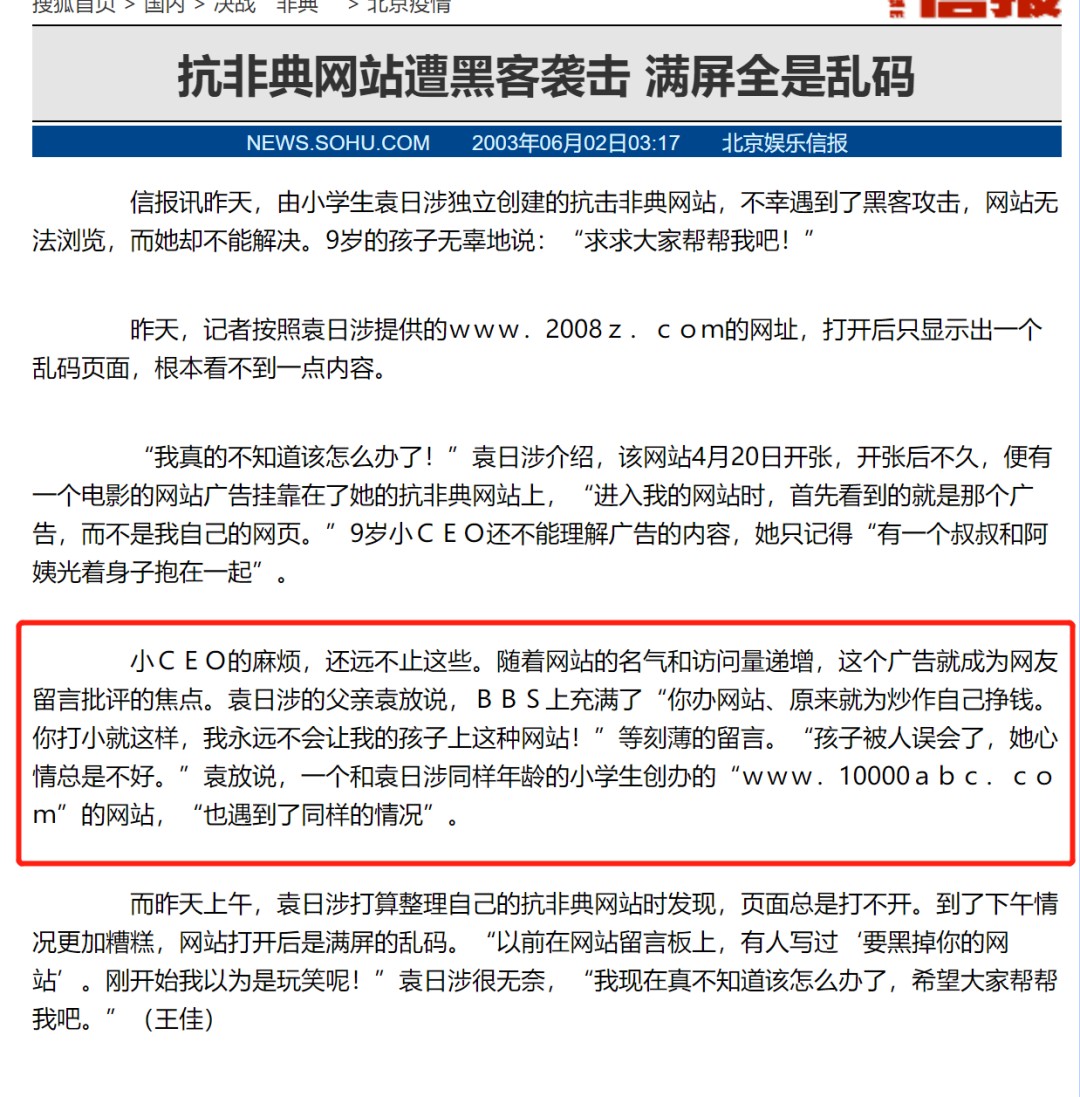
其实在2020年就有人回忆过2003年,作者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将其定义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重要一年。刘强东、马云、马化腾都被描述为了超前的“洞察者”,大胆地把“环境上的限制”转化成了“弯道超车的机会”。作者在引言里感慨地说:“鏖战瘟疫的同时,也许新的机会又在灾难中慢慢形成”。
不知道陈天桥喝不喝得下这碗鸡汤,毕竟那时候的赢家其实是他和史玉柱,他们做的生意比东哥、Pony更适合“战疫新环境”,都登上过胡润富豪榜的顶端,甚至也成为了类似文章的主角。
那是《三联生活周刊》发表在2002年底的人物群访,标题叫《上海没有冒险家》,陈天桥实名吐槽了“结果预设在那里,说什么都有道理”的舆论风向:“《传奇》开始推广的时候,有人评价是个烂游戏;然后说游戏是个好游戏,可惜一个烂公司在做;最后也不说公司如何了,就说我们是捡了一个大元宝。”
只能说“人没有办法想象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或者“人只相信自己经历过的事”。大数据这个概念在2013年之后才开始流行,中国智能手机换代高峰期,官方定义的时间线是2013至2015年(来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在这之前,没有算法“腻缝”,过载的信息可以用“真随机”的姿态出现在每个人的面前,如果不抱着善意主动给难以理解的行为上点价值观,对于个体就显得相当残酷。
至于你问非典型、湖北小伙、“海湾那旮沓挺闹心”呢?还是别难为我了。贴吧还在封闭开发,阿北应该还没有写好BP,这些本来就有参与门槛的话题,在那个春天还没找不到机会接受“社交网络传播规律”的改造,我也不知道应该共情谁。
春天很短。实在好奇,问家大人去吧。








